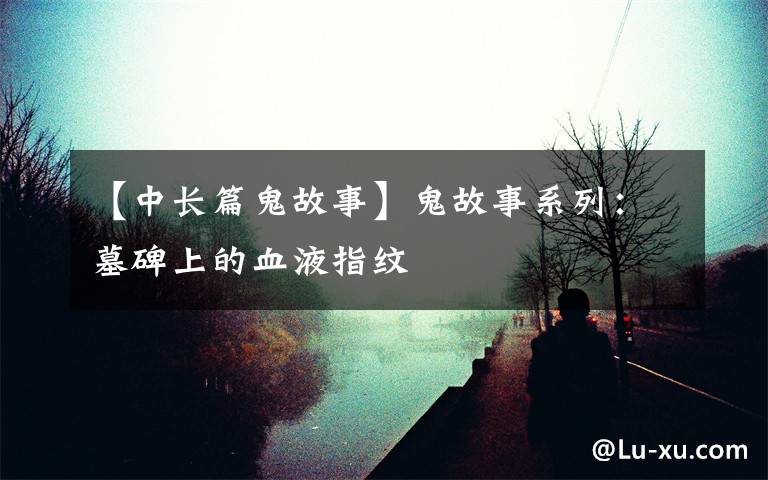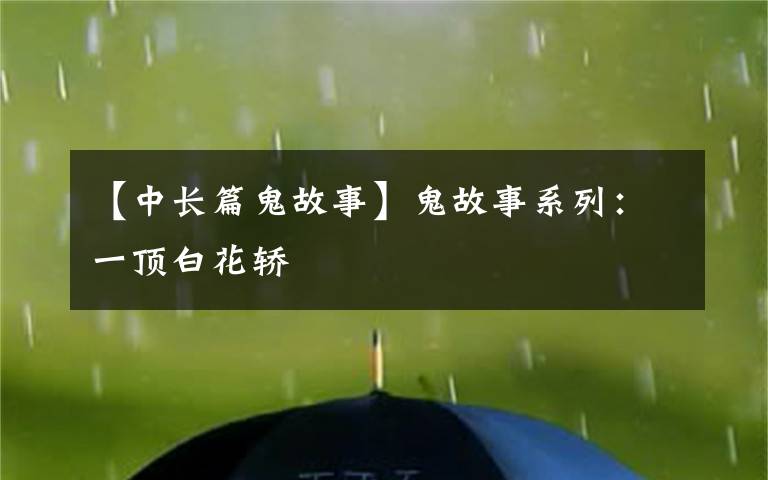鬼小七奇谈: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,一对年轻的夫妻,他们原本生活的很美好,但是,万万没想到在最后竟然会变成这般模样。一切都得从她考上公务员开始说起,她每天都在说错话,所以这对夫妻开始分析话语中的各种深意,但是,在最后,这种分析也害死了他们。究其原因裂痕的产生不仅仅是外在的刺激,更多的还是人的内心,敏感、多疑,他们终究没有逃脱。
将近黄昏,我提着从超市买来的东西,从603路车下来,沿着马路朝前走。再朝前走几百米,就是我刚搬进去的画苑小区。我放慢脚步,左右两腿一步一挪,低着头数人行道上的地板砖。我的影子拖在前边,每一步都踩在影子上。
我的速度慢得有些离谱,这从路边人们诧异的眼神可以看出来,他们一阵风似的从我身边经过,有些好奇心特别强烈而又不知道掩饰情绪的人,瞪大眼睛看着我,几个刚放学的女孩聚在一起对我指指点点。
这些女孩的留海都盖过了眼睛,宽大的校服上顶着一张雪白的脸,让我想起日本鬼片里的主角。
经过小区门口的理发店时,从玻璃门上看到自己:前倾的身体,一手提着一大袋东西,要死不活地朝前挪动。不怪别人觉得奇怪,连我自己看了这副样子,也觉得很不正常。
不知不觉,就走到了小区门口。我站在大门前,那门上似乎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在阻止我进去。我站了很久,从我身边的经过的人都回头看我,保安从狭小的玻璃房里走出来几次,似乎想问我什么,又回去了。
站的时间越久,我越觉得自己不能进去,于是又转身,沿着来路走去。
来来回回走了很多次,两只手已经被沉重的塑料袋坠得失去了知觉,人们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的时间越来越长,我沉重地来回行走,从车站到小区门口的路边或许被我碾平了不少。
又一次往小区走去时,我忽然感觉肩膀上沉甸甸的,似乎有什么东西压在身上。仰头一看,正看到我家的窗口。它本来拉着窗帘,关得紧紧的,现在完全敞开了,沈湘的上半身出现在窗口,穿着绿睡衣,头发披在脸的两边,露出一张很窄的脸,显得异常苍白。
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我加快脚步朝前走,勉强露出一个笑容,把两只塑料袋集中到一只手上,朝沈湘挥了挥手。沈湘一言不发,随着我的行走,她的身体也在转动,像风向标一样,始终把一张狭窄惨白的脸朝着我。
暮色已经很浓,衬得沈湘的脸更白。别处的窗口早已亮起了灯,只有我家的窗口,依然浸泡在黑暗中。想到我即将进入家门,便觉得失去了所有的力气。然而我无力逃脱,就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绳索套在我的脖子上,窒息,但我很顺从。
进了小区的门,走出沈湘的视线,身上磨盘压顶的感觉消失了。我略微放松了一下,把脚步放慢,低着头,拖拉着往前走。
走到花坛边,我忽然觉得再也没有力气走下去了,便放下塑料袋,自己坐在石椅上,从口袋里掏出烟猛抽起来。烟头忽明忽暗地燃烧着,陆续有人从外边走进小区,有人在大声呵斥着自己的孩子和丈夫,听着这声音,我产生了强烈的嫉妒。
那种磨盘压顶的感觉又来了,我慢慢抬起头,在厨房的窗口,一张脸浮现在黑暗中,看不清容颜,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和黑暗融为一体了,不过我知道那是沈湘。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——我坐在一棵柳树下,浓密的枝条垂在我的头上和身上,遮住了我的大半个身子,不妙的是我在抽烟,烟头在黑暗中是个醒目的红点。
我匆匆掐灭烟头,提起地上的塑料袋——塑料袋是白色的,这又是一个醒目之处,何况沈湘会计算时间,她一定能算出我进入小区后曾经在这下面逗留了很长时间。
我又打了个寒颤。
客厅里没有开灯,我小心地把灯打开,没有看到沈湘。走进厨房,她仍旧站在窗口前,背朝着我,一头漆黑的头发直得仿佛做过离子烫。绿色的睡裤有些短,露出她白色的脚踝。
我深深吸了口气,酝酿了一会情绪,飞快地走到她跟前,举起手里的塑料袋,轻快地说:“看我买了什么?”
她没有任何反应,两边的脸颊被头发遮住,只露出中间狭窄的一条,仍旧凝视着楼下的什么地方。我硬着头皮,继续欢快地道:“过来看看。”我拉着她的手,把她拉到餐桌边。她没有抵抗,直接跟过来,木然站着。
我把塑料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:“看,蒙牛的大颗粒酸奶,特意买给你的——芒果,你不是喜欢吃芒果吗?我买了很多…...”我絮絮叨叨,一刻不停地说着——说这些是安全的,不会出现意外,我被紧锁的喉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,我尽量让它们恢复弹性——不仅如此,我也害怕停顿下来会陷入可怕的沉默。
“唉…...”沈湘毫无预兆地叹了一口气,我觉得背后一凉,似乎有种软弱无力的东西正顺着脊柱爬上来。我的动作停顿了一下,接着,又继续往外掏东西,正打算再次喋喋不休,沈湘按住了我的手。
我不得不抬起头来看着她。她乌黑的眼珠凝视着我,我却盯着她白眼球上的一丝血丝。她凝视了我许久,我眼睛一霎不霎盯着她的眼珠,不敢看她的脸。
“下班后为什么不马上回来?”她幽幽地问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沈湘说话变成了这种幽灵般的腔调,特别轻,似乎不是从实体中发出的声音。
“哪里,我不是去超市买东西了么?”我的脸忍不住抽搐了一下。
“下班的时候,我在窗口等你,我看见你提着东西走到小区门口又转身走回去,你来来回回走了有十几趟,后来我忍不住了才走到窗口露出脸来。”她说。
她的声音没有抑扬顿挫,仿佛不带感情,听得我一阵难受。我不由有些恨她——明知道这么问下去会发生什么事,她为何非问不可呢?即使不是为了我,为了她自己,她也该聪明地缄默才是。
她应该知道我已经尽力了,我也只是普通人,我也会偶尔需要释放自己的情绪——这些话在我心里翻腾着,我吞了口唾沫把它们咽下去,笑了笑,轻声道:“哦,我只是在想事情,你知道的,我想事情就喜欢来回走动。”
“是在想我吗?”她问。
“不是!”我飞快地回答。
咔嚓。一声不易察觉的响声在屋子里响起,就像什么地方磕破了一个鸡蛋。我心惊肉跳地看着她——她的下巴上出现了一道一寸来长的血丝。
仍旧是如此,不管我多么努力,还是避免不了这个。我绝望地看着她——你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答案呢?昨天,也是同样的事情,她问了同样的问题,当时我的回答是“是”,她的脸上出现了血丝——今天我作了相反的回答,仍旧如此,无论我怎么回答,其结果都是一样的。
“又一条。”她说。
“我究竟该说什么,才不会出现这个?”我忍不住问。
咔嚓。
这次是鼻子,一道细细的血丝出现了。
“又一条。”她哀怨地看着我,眼睛里慢慢流下眼泪。她把流着泪的眼睛凑到我面前,盯着我,眼睛里拿道血丝显得格外触目惊心。
她慢慢抬起手,我恐惧地看着她——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,可是我不能离开,只能停留在原地,任由她两只手掌插入两鬓,把漆黑的头发挑起,仿佛帐钩挑起蚊帐,她两侧的脸颊露出来了。
我叹了一口气。
咔嚓。
她额头正中央又出现了一条血丝。
我再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,听凭她拿起我的手,在她的脸上游走。我的手指能感觉到她细腻的肌肤,但更多的是伤痕——累累伤痕重叠在她雪白的脸上,就像有人曾经用小刀在她脸上割上无数细小的纹路。
两颊的伤痕最多,面部中央也有,但不那么明显。不管怎样,这样一张脸看上去很吓人,而她始终凝视着我,我甚至不敢露出恐惧的表情。
“你数数,多少道了,一大半都是为了你。”她幽怨地道。
“我知道你对我好。”我苦笑道。
她难得地展开一丝微笑,把头贴在我胸口。我抱着她站了很久,手和腿脚都发酸了,也不敢动弹。直到她主动直起身来,笑着说:“我饿了。”
“我去做饭。”我松了口气,提起东西走进厨房。
沈湘没有跟来,她不喜欢进厨房,这里是我唯一可以喘息的空间。我一边切菜,一边忍不住想:我的生活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?
我不能说任何伤害沈湘的话,否则她脸上就会出现血痕——那并不是普通的伤痕,凑近了看,可以看出,那是一道细小的裂痕,皮肤朝两边翻开,露出里边鲜红的肉来。并没有鲜血流下,但因为里头裸露的红色翻了出来,看起来就像是血痕。
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之前,沈湘还很正常。现在她看起来像个幽灵,在这之前,她活泼开朗,一点异常的感觉也没有。
情况是从她换工作开始的。毕业后好几年,沈湘一直在广告公司打工,我们结婚后,打算要个孩子,而广告公司持续的熬夜加班无法适应这项计划,于是沈湘报考了公务员。半年后她被录取为市政府的办事员。
上班的第一天早晨,沈湘很兴奋,但到了下午,当我下班回来,发现她正无精打采地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。
“看样子情绪不高啊?”我笑着摸了摸她的头。
她的表情很郁闷,低头沉思了一会,转头望着我:“石头,你说,我是不是一个口没遮拦的人?”
“当然不是,怎么了?”
她抿了抿嘴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: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,我真的没说什么特别的话,可是张大姐生我的气了,他们都说我得罪张大姐了。”
“你说什么了?”我紧张地问。张大姐是他们宣传科的科长,在机关部门,得罪了领导可不是什么好事。
“我不知道,”沈湘泪汪汪的,“我问别人,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。反正我只知道我得罪她啦!”
那天我们没有做晚饭,两人都没有心情,这种情况让我们很紧张,我们一人抓了个馒头,打开一盒鲜奶,边吃边分析张大姐到底因为什么生她的气。沈湘翻来覆去地回忆白天说过的每一句话,我把那些话都列在纸上,左分析右分析,提出各种可能,直到深夜,依旧没有找到答案。
第二天,沈湘上班前有些发怵,我使劲鼓励她,她才忧心忡忡地出门了。
下班回来,沈湘又是一泡眼泪。她红着眼睛坐在沙发上写着什么,面前的茶几上散乱地放着十几张写满了字的纸。我注意到她没有换上拖鞋和室内服装,看她头发散乱的样子,便知道又出问题了。
“又怎么了?”我问。
她用手指指桌上那些纸,不说话,仍旧低头狂写。
我随手抄起几张纸一扫,上头写的是些对话,是沈湘和不同的人的对话纪录。我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——和昨天一样,沈湘肯定又不小心得罪人了,她正在回忆和每个人说的每一句话,以便分析这其中的原因。看她奋笔疾书的样子,一股寒意从心中升起,我按住她的笔说:“别写了。”
“不行,”她带着哭腔说,“我就是要看看,就是要看看,怎么才两天功夫,我就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?”
这个说法让我暗暗心惊。沈湘的感觉我很理解,她对这份工作十分重视,在如今动荡不安的就业环境下,像沈湘这样的本科生太多了,她的才华和背景都殊无可道之处,连一般女孩都有的野心和欲望也不充足,唯一的希望就是平安平凡地过下去。
公务员的工作很稳定,待遇也高,让她有了久违的安全感。但刚上班就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,这确实不是好现象。我拿起那些纪录仔细看起来,看了一阵,我再次让沈湘停下来。
“这个苏岩是什么人?”我指着一张纸问。
“我们办公室管电脑的。”她头也不抬地说。
“你和他说话很少。”
“对,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网聊,不喜欢说话。”
“别写了,”我再次按住她的手,“我们就从这个苏岩的对话来分析一下,他的话少,只有5、6行,容易分析。”
沈湘的目光一亮,难得地露出了笑脸:“真的,我怎么没想到?”她立刻活泼起来,拉我坐在她身边,在我脸上亲了一下。
沈湘和苏岩一共只说过三句话。沈湘早晨进办公室,对苏岩说:“早。”苏岩头也没抬望着电脑说:“早。”当时办公室其他人还没来,沈湘又说:“这么早就上网啊?”苏岩望了她一眼说:“嗯。”
过了一会,人都来了,有人问谁最早来,沈湘说:“苏岩最早来。”苏岩没作声。到下午,大部分人,沈湘发现自己得罪了不少人,努力想挽回局势,主动给大家擦办公桌,擦到苏岩的桌前时,她讨好地说:“苏岩,你的办公桌真干净!”苏岩起身就走。
就是这么几句话,我们分析了半天,沈湘觉得自己没有说错任何话,我也觉得她没有说错什么。但是,从苏岩的角度考虑,加上是在市政府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,我认为沈湘的那句“这么早就上网啊”就是罪魁祸首。
“为什么?”沈湘不解地问。
“首先是从反应来看,你跟他说早上好的时候,他也回了一句问好,显然这句‘早’并没有得罪他。而当你说‘这么早就上网啊’的时候,他看了你一眼,这一眼很可能有别的含义,至于那句‘你的办公桌真干净’,这完全是夸奖的话,他不存在生气的可能,所以,只有第二句话才有可能让他生气。”
我说,“至于这话为什么会让他生气,我猜可能他误以为你的潜台词是在指责他成天上网耽误工作,虽然你们那单位清闲,大家都没什么事忙,但这话不能公开说,你说是不是?”
沈湘连连点头:“肯定是这样!”
我觉得有点饿了,可是沈湘很兴奋,顾不上吃东西,又让我分析其他人的话。
那晚我们都没有吃饭,在疯狂的分析中沈湘学会了抽烟,一直到凌晨四点,才体力不支睡了一会。早晨出门时,她眼睛里还带着血丝,神情却很兴奋,她说她一定会改变这种局面。
但实际情况是,她再次兵败而归。
我已经习惯了沈湘在下班后蓬头垢面地疯狂书写对话纪录,然后帮她逐一分析。她乐此不疲,但我却很快就厌倦了。这是一项会让人发疯的工作,我们陷入对话的泥沼中,在那些再正常不过的话语里寻找别人生气的蛛丝马迹,却又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。有时候我想告诉沈湘这种做法徒劳无益,但看到她的眼泪,我又把话忍住了。生存不易,沈湘也是没有办法。
我后来经常想,沈湘最终变成如此模样,和我的纵容也脱不了关系。
沈湘和同事们之间的对话,在我看来其实毫无可疑之处,只有精神病人才会对这些话生气,可是她的同事们偏偏都生气了,这让我感到无法理解。倘若仅仅是如此,那倒也罢了,可怕的是,在这种无限的分析和猜测中,沈湘也在一步一步的改变。
她变得敏感而多疑,有时候,我无心的一句话,就会让她想到很多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地方,并且列在纸上进行分析。
第一次发现沈湘的这个毛病,是在沈湘又一次让我帮她分析那些对话时。我发现其中一张纸上写的是我和沈湘的对话,不由惊讶万分:“这是怎么回事?为什么把我和你的对话也记下来?我没有生你的气啊!”
“是吗?”沈湘狐疑地看着我,“可是我觉得你生气了。”
“我没有。”我哭笑不得。
“如果你没有生气,你为什么说你累了?”
“我是真累了。”
“可是你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”
“那是因为我以前没有觉得累。”
“以前没有累,为什么现在累了?是不是对我厌烦了?”
“怎么会?是最近工作压力大,再加上睡得晚。”
“啊?你终于说了,是因为睡得晚!是我害你睡得晚,是不是?”沈湘的话一步紧似一步,我眼冒金星,头疼欲裂,按着额头说:“我不是这意思。”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?”她质问道。
“我就是累,仅此而已,你别想多了。”我疲倦地说。
“我想多了?你的意思是所有这些都是我想多了?可是他们确实都在生我的气,怎么能说是我想多了?”沈湘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流下来。
“我没有那么说。”我筋疲力尽。
“你没有那么说?那么还是我自己在瞎想喽?”
……
这样鸡蛋里挑骨头的争吵一日盛于一日,沈湘后来也不分析她和同事们的对话了,转而抠住我话里每一个漏洞进行攻击,大部分时候是她自己无中生有的臆想。这种毫无意义的争吵让我感到厌烦,我们经常吵架,甚至提到了离婚。
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,我们还会这么继续吵下去,直到分手。
那天下班后,我在厨房里做饭,沈湘在看电视。饭菜摆上了桌子,沈湘走过来问:“今天做的什么菜?”
“就这些,你自己看。”因为连日吵架,我没有心思哄她。
这句话的语气如此冷淡,沈湘显然感觉到了。平时就算是我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她也能挑出毛病,何况此时真有问题。她眉头一耸,看来是要像往常一样开战,就在此时,我们都听到了“咔嚓”一声轻响,仿佛什么地方磕破了一个鸡蛋。
沈湘的左脸出现了一条血痕。
“你脸上怎么回事?”我连忙凑近去看。
“别碰我!”沈湘摸了摸左脸,还在生气。
“不碰就不碰。”我把手缩了回来。
咔嚓。
又是一声轻响,她的耳朵旁边又出现了一道血痕。
这下我觉得奇怪了:“沈湘别闹了,真的,你看看你的脸。”
“我的脸怎么了?我哪里闹了?”沈湘恼怒地说。与此同时,又是咔嚓一声,又一道血痕出现在她脸上。
我开始感到惊慌,不顾她的反对,把她拖到镜子前,看到镜子里的自己,她也慌张了: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
“我不知道,是不是什么真菌感染?”我慌乱地说。
“那我们去医院。”沈湘手忙脚乱就要朝外走,我一把拉住她:“医院的专家门诊现在不开,你去也只能看急诊。”
“难道就这么呆着?”她问
“我不知道,再等等看?”我试探着问。
咔嚓,又一道。沈湘愤怒地捂着脸看着我:“再等等?你是不是不关心我啊?”
毫无意义的争吵又展开了,我每说一句话,就能听到咔嚓一声,沈湘的脸上就会出现一道血痕。后来我终于发现这个,连忙闭上了嘴,任由她怎么骂也不开口,血痕总算是不再出现了。
这个发现让我觉得十分怪异,这显然不是正常的事。等沈湘睡着了以后,我试探着对她小声说话,但并没有看到血痕出现。
也许,今天的事只是巧合?
我疑惑地睡着了,沈湘就睡在我身边,脸上是几十条血痕。这些血痕覆盖了她小半边面颊,让她惊恐欲绝,简直有些歇斯底里了,我给她吃了两片安眠药她才安静下来。
第二天,沈湘没有去上班。如此多的伤痕在脸上,她没法出门。跟单位请了假,我陪她去医院看了看,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,随便开了点消炎的药,我们就回来了。
一路上我尽量不说话,偶尔说上一两句,也会提心吊胆地看着沈湘的脸。让我不解的是,在我说完话之后,有时候她脸上也并不会出现血痕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
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三天,沈湘脸上的伤痕在持续增多,她近乎绝望,经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,眼睛望着墙。我们本以为如此细小的伤痕很快就会自行愈合,但它们似乎从来不愈合,旧的伤痕永远像新伤痕一样鲜红。后来,我壮着胆子跟沈湘提议用放大镜看看这些伤痕,沈湘凝视了我半天,才慢慢点头。
在放大镜下,这些伤痕被放大了数十倍,这样它们看起来就不像伤痕了,而像一条条的裂缝,露出里头鲜红的肉来。我把这个发现告诉沈湘,她的目光更加黯淡。
伤痕——或者该说是裂缝——裂缝不断出现在沈湘脸上,她的脸仿佛随时会碎裂。这种情况让我们都陷入了恐惧和绝望之中,我们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而在这段时间里,我们仍旧未停止争吵。无论我说什么,总是能让沈湘怀疑到其他地方。因为她的病,大部分时间我都保持沉默,但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反击,而每当我反击时,我就会看到那些裂缝一条接一条出现在沈湘脸上,咔嚓咔嚓之声不绝于耳。
我终于明白,原来是那些让沈湘感到刺耳的话令她的脸上产生了这种裂缝。这个发现让我不寒而栗,我犹豫了很久才把这个发现告诉沈湘,她蓦然瞪大眼睛:“原来是你在害我!”我感到气愤——她怎么能这么说呢?但我不敢反驳——一反驳,她必然会生气,而只要我的话让她生气,她的脸上就会出现裂缝。
于是我只好小心奉承讨好沈湘。在我的小心讨好下,沈湘脸上的裂缝增加速度明显减慢了。但原有的裂缝仍未消除,她没法再去上班,很快就被单位开除了。
她一个人坐在家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,总之,她日渐地改变,终于变成一个怨灵般的女人。她始终温柔地对我说话,当我的话伤害到她时,她便露出极度哀怨的表情,向我展示她的伤口。
我正在回想这一切时,身后传来一团幽冷的气息,沈湘幽幽地问:“在想什么呢?”我这才发现,开着的水龙头一直在流淌,水已经从洗菜的池子里溢了出来,流到了地上。我连忙关了水龙头,拿拖把拖地。
“没有想什么。”我对沈湘说。
咔嚓。
这声音让我心惊胆战,我浑身抖了抖,只听沈湘幽怨地说:“你明明在想事,为什么不承认?”
我该怎么回答呢?
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怎么回答都是错,怎么回答,裂缝都会出现。
嗯,我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。我小心翼翼地斟酌每一句话,沈湘要如何便如何,我从来不反驳她,也从来不敢对她高声。我习惯了像女人一样细声细气地说话,也习惯了长时间地沉默。是的是的,只要这个女人的身体上不再出现裂缝,所有这些我都可以习惯。
咔嚓咔嚓咔嚓。
可是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,反而是越来越快了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,我已经如此小心,裂缝出现的频率却越来越高。这声音让我心惊胆战,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只惊弓之鸟。每天出门,是我最快乐的时候,而回家,总是如此艰难。
我为什么不离婚呢?
我想离婚,真的,很想,特别想,可是我不敢说——我不敢想象,当我说出“离婚”这两个字时会发生什么事,也许,她会真的裂成两半?
时间就这么一秒一秒、一分一分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、一天又一天地缓慢流淌。每一天都是煎熬,我不明白这样生存的意义何在。我害怕沈湘,她就像是日本鬼片里那种幽怨的女鬼,死死缠住我,我总有一天要被她缠死!
可是,即使是如此厌恶和害怕,我却仍旧不能拒绝她求欢的要求。当她抱住我发出呢喃时,我只能强打精神作出回应——裂缝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她身体的每一部分,她遍体都是细小的缝隙,一道道的鲜红交织成一张网,网住她的雪白。我对这样的身体毫无欲望,而我的冷淡反应又让更多的裂缝出现。
咔嚓咔嚓咔嚓。
咔嚓咔嚓咔嚓。
我想我真的还不如死了好。
其实我是个很善良的人,真的,我发誓我是个善良的人。可是善良是那么一种脆弱的东西,它经不起如此长时间的扭曲和挤压——实际上沈湘本来也是个很善良的人,不是吗?
说到底,我们都是受害者。但我再也没法忍受了,这种变态的生活,这种像走钢丝般小心的对话,让我的神经高度紧张,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求死亡。
假如我和沈湘一样不出门,就这么呆着,那么我也许早就死了。但我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,在单位里有很多朋友,每天,我都能看到生活向我展开繁华的面貌。离开家门,我就开始眷恋生活中的一切,而一走进家门,我就觉得走进了坟墓,我与鬼同屋。
生存还是死亡?我无时无刻地想着这个问题,家和外面的世界,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召唤着我。我这么年轻,这么强壮,最终,我仍旧是想活下去。
不仅要活下去,而且要好好地活,不是这样被柔软灰尘埋没和窒息的日子,不是用我余下的美好生命和一个女鬼陪葬。
那么,沈湘就必须死!
第一次产生这个念头时,我打了自己几个响亮的耳光。我觉得自己如此很狠毒,简直不是人。可是就在此时,沈湘幽灵般走进来,哀怨地问我为何要扇自己耳光。我说不出理由,她步步紧逼,身上咔嚓之声不断。
这让我下了决心。
我再次发誓我是个善良的人,今后我也会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,但我,但我必须杀了沈湘!
杀死沈湘是最简单的事情,除了勇气,我不需要做更多准备。
我用了一个星期来努力对沈湘好,不过这丝毫不见她有什么反应——实际上我对她已经不可能更好了,再过去的那些日子里,我极尽温柔和忍让之能事,而她始终觉得我在伤害她,现在也没有任何改变,她依旧觉得我在伤害她,她身体的缝隙密密麻麻,红得耀眼。
一个星期以来,我的心一直在剧烈地跳动,我希望突然出现奇迹,但奇迹没有发生。一个星期后,我的心跳忽然恢复了平静,走进家门的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冷静得像个职业杀手。
和往常一样,屋子里没有开灯,沈湘鲜红的脸在黑暗中模糊一片。我把灯打开,她穿着绿睡衣,站在客厅里望着我。
“你回来了?”她不知道将发生的事,仍旧和往常一样幽怨地问。
“你知不知道你很像鬼?”我舔了舔嘴唇说。
咔——嚓!
这声响格外剧烈,我看到沈湘露出震惊的表情——我从来没有这么对她说过话,这么久以来,她已经习惯了我温柔,我看到这句话产生的巨大冲击——她的脸上出现了一道前所未有的大裂缝,大概有一支圆珠笔那么粗那么长的裂缝,咔嚓一下就出现了,就像脸上被人猛然劈了一刀。
我有些心悸,有一个瞬间,我甚至想终止我的计划。但,看到她脸上的裂缝,我又下定了决心——我不可能和这样一道裂缝同床共枕,那样真是生不如死!
“你看看镜子,你知道你多有多丑么?”我继续恶毒地说。
咔嚓。
她敞开睡衣,从肩膀到腹部,一道巨大的裂缝出现在她身体上。她在剧痛中凄惨地嚎叫起来。
“我早就讨厌你了。”我飞快地、不停嘴地朝下说,“你自寻烦恼,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是你自己疑神疑鬼,我对你这么好,你没有半点感激,反而处处刁难,我欠你的吗?你有什么了不起吗?你……”我头脑兴奋而空白,各种毒药般的语言迅速从嘴里飞出。
裂缝,一道又一道裂缝出现在她身体上。纵横交错,她的手臂摇摇欲坠,终于掉了下来,她的耳朵掉了,接着是大腿……凄厉的惨嗥掩盖了咔嚓之声,掉下来的躯体仍旧在产生新的裂缝,她的脸终于在五道裂缝的综合作用下分崩离析。
我看到她最后露出的表情仍旧是哀怨——没有恨,只有哀怨——她碎裂成无数的碎片,我满头大汗,心跳如鼓,仍旧在骂——碎片又碎成更小的碎片,继续碎,继续,直到完全消失,再也没有动静。
安静了。
彻底的安静,再也没有咔嚓声,再也没有幽怨和哀愁,地上一堆灰尘样的东西,就是我曾经的妻子。我拿扫帚把它们扫作一堆,扔进垃圾袋里。
我提着垃圾袋出门——天空是黑色的,霓虹灯四处绽放光彩,人们语声喧哗——生活真美好,我把垃圾朝前一抛,大声说了句什么。
真美好,就像脱去了一件紧身衣。
我的兴奋之情持续到早晨,一直到上班,到公司,我始终精神焕发。
公司同事小李说:“石头,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?”
我的情绪忽然就沉到了谷底。
他为什么这么问?
难道我的情绪这么明显?
他是不是知道什么?
我死死地盯着小李,他脸色变了,有些紧张地后退:“石头,你别这么看着我。”他转身跑了出去。
叫我别这么看着他?为什么?他讨厌我吗?
咔嚓。
这熟悉的声音让我全身一阵,我跑到洗手间,镜子里映出我惨白的脸,下巴上,一道细小鲜红的裂缝,像血痕般出现在那里。
(完)
想要知道更多惊悚、重口、探索故事,可加微信“每天一则鬼故事”关注更多鬼事!
1.《【中长篇鬼故事】长篇鬼故事:脆弱敏感的人类,破裂最终是因为它》援引自互联网,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,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与本网站无关,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。
2.《【中长篇鬼故事】长篇鬼故事:脆弱敏感的人类,破裂最终是因为它》仅供读者参考,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,对其原创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。
3.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,https://www.lu-xu.com/guonei/2241123.html